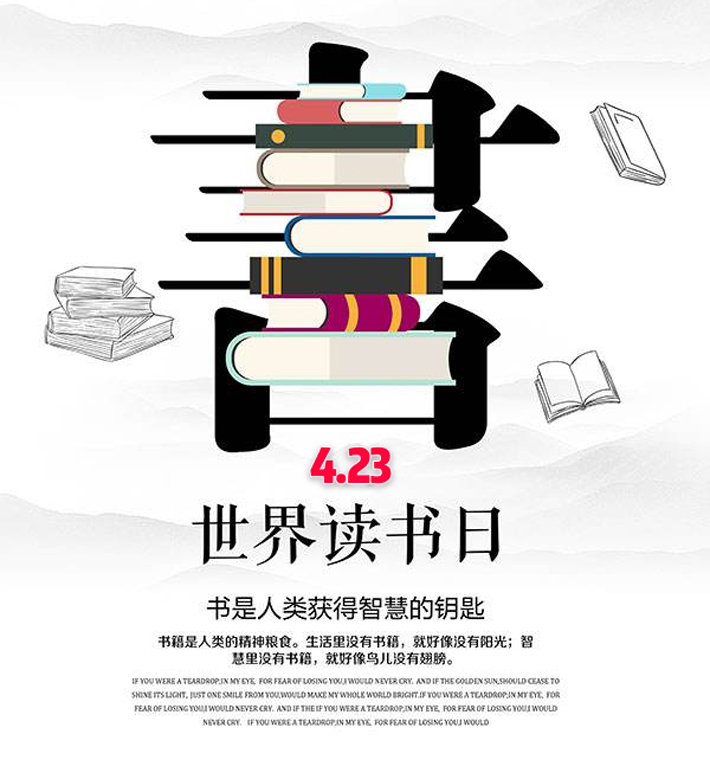
人说三岁看老,每次听见小孩子说起自己的鸿鹄之志来,我心里就惭愧。说来好笑,我小时候的志向没出息得很,只巴望能去图书馆做个管书的,不花一分钱,坐在书堆里,那就是神仙岁月了。
跟着岁月脚步往前走,渐次明白,书,不是张望大千世界的唯一的窗口。可骨子里痴心依旧,有时不免想,贾宝玉“抓阄”时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,要是我,恐怕会再腾出只手拿本连环画来翻翻。后来读杨绛的《将饮茶》,知道了钱钟书名字来源于周岁试儿时抓了本书。我不由大为懊恼:原来前贤早有榜样,我的淘气空想岂不成了东施效颦。
儿时的心愿颇有几分以图书馆为家的豪迈气概。不想看了几本古今中外的书,反而“英雄气短”,颠倒过来,一心要以家为图书馆。不分精细,不论贵贱,只顾着同购物狂一般买书。长辈们惊问缘故,我堂堂皇皇地大吹法螺:画家搜尽奇峰打草稿,我腹中空空再不网罗 天下好书只怕连文章的草稿也拟不出了。父母信以为真,想不到孩子这么明理,不需耳提面命就开了窍——唯有读书高,欢喜得恨不得再为我添两个书架。倒是爸爸冷眼旁观了几次,看出蹊跷所在:有些书你怎么只买不看?亚里斯多德的《诗学》、贺拉斯的《诗艺》经年累月地晾在角落里,大部头的《史记》蒙难囚禁……我只好坦白,不如此, 怎么布置得了一个像样的书房呢? 纸笔在案,书卷横陈,是翰墨飘香的中式书斋;宽大的书桌,整齐排列的精装书,则透出欧洲的浪漫情调。两者虽情趣迥异,共同点不都是藏书无数吗?!我舌灿莲花地自己辩解一番。换来的评价却是“叶公好龙”。冷静一想,这种行为实质上和《围城》里的那位“你我他”小姐相去不远。我的“中西合壁式书房” 慢慢恢复了秩序,不再是辅天盖地的书库模样,毕竟是凡夫俗子的寻常居室,无法变作多多益善的图书馆。
读书之乐如何似?有两句现成话儿作答:有好友来如对月,得奇书读 胜看花。其实,最佳境界已被《红楼梦》里的政老说得十分透彻。对着潇湘馆的千竿修竹、大株巴蕉,这位迂腐古板的老爷也慨叹:“若能月下坐此窗下读书,也不枉虚生一世。”都市里无处去觅如此幽静脱俗的居所,好歹境由心造,窗前落叶,几上文竹, 也足以营造氛围的。
过去有句话叫:演戏的是疯子, 看戏的是傻子。写书的和读书的又何尝不是呢?!十来岁时迷书信书,看了林黛玉教香菱作诗时说的,只要把王维、杜甫、李白的诗读一二百首作底,再把陶渊明、谢灵运等人的作品一看,不用一年工夫,不愁做不得诗翁。真真美煞了我这个“诗迷”,冲看一年速成的魔力,我当真死心眼地添置了十几部诗词曲赋经典著作,成日念念有词。一年之期转眼即至,显而易见我还是我,半个诗翁都不曾做得。快快地去请教师长,先生大笑: “谁叫你读《红楼梦》走火入魔,那毕竟只是小说家言嘛!”时至今日, 我还常纳闷为什么大观园里的女孩子作诗一个个无师自通,而且妙笔生花。再回头看看自己的歪诗,总透着今人穿古装的味道。
爱书人都言最喜坐拥书城,可有时回首望见家中那堆积成丘的“进步的阶梯”,我又无奈起来,也许,腹笥宽广是要以生有空间来换取的吧。明月当窗时,也只有以“屋宽不如心宽”来自我解嘲了。










